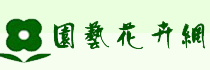
黑木奈奈12月9日,初雪苏州,在古城区连绵不绝的黛瓦上留下薄薄的一层白痕。化雪时分,最是寒意逼人,王澍、董豫赣、王欣等十多位建筑学者、建筑师、园林专家不辞风雪,齐聚拙政园。此次的契机,是童寯的英文旧著《东南园墅》中文版再版上市。本书、童寯之孙、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童明表示,上一次如此规模的建筑界同仁共聚一堂研讨中国古典园林已经是11年前的事了。 在拙政园举办《东南园墅》研讨会,格外有意义。遥想大半个世纪以前,童寯为了从事江南园林研究,频繁利用周末去苏州访园,他或许也曾在某个雪日的午后到访拙政园,被江南园林之美所倾倒。童寯(1900年-1983年)是从美国大学建筑系毕业归国的首批中国建筑师之一,他从1930年代初开始从事江浙一带的中国古典园林研究,是我国近代造园理论的开拓者,与吕彦直、杨廷宝、梁思成、刘敦桢并列被为中国“建筑五师”。 根据童明的介绍,童寯针对江南园林的研究最初是用英语写就的,其目的是向介绍这一中国文化瑰宝。中国虽然有悠久灿烂的造园传统,但长时间以来鲜有人系统性地进行园林研究。中国造园艺术早在18世纪就已经影响到欧洲,法国人甚至创造了“英华园庭”(Jardin Anglo-Chinois)一词,但到了20世纪上半叶,积贫积弱已逾百年的中国早已了这种影响力。彼时对东方园林的认知似乎仅限于日本,为了更正这种观点,明确日本园林的根源在于中国,童寯发表了《中国园林——以江苏、浙江两省园林为主》一文。 1936年至1938年间,童寯每年为上海《天下月刊》撰写三篇英语论文,向英语读者介绍中国建筑传统和演变。在他的园林研究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他用一种比较的眼光将中国园林置于世界园林的语境内进行分析。童寯运用现代建筑学知识去剖析园林的实质,他在上海、苏州、无锡、常熟、扬州及杭嘉湖一带花费大量精力实地探访,进行园林调研测绘和拍照,发表了大量相关研究。童寯的《江南园林志》被学界为继明朝计成《园冶》之后,在园林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也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最早一部运用科学方述中国造园理论的专著。从1937年发表《江南园林志》到1983年临终前在病榻上亲手校订完稿的《东南园墅》,终其一生,童寯都在通过研究园林来思考如何从传统中吸取精华,发展出属于中国自己的现代建筑。与此同时,专门针对中日园林之间的传承与差异,他也在多篇著作中探讨相关问题。 中日两国园林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差别的关系或许还是这两国的人最能体会。1923年开始,日本作家村松梢风(他也是首位称上海为“魔都”的人)几乎每年都要造访中国,他为江南的秀美风光所倾倒。在1928年发表的《中国》一书中,村松梢风讲述了他在游览了杭州西子湖畔的别墅式宅邸,首次领略中国园林之美时的: “中国的庭园宜于从外面观看,这是与日本的庭园在意趣上不同之处。日本的庭园是宜从屋内、从席地而坐的客堂上望出去的园林,任何一座名园都是依此而设计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日本庭园用白色砂砾拖曳出波浪、其间用石块点缀的枯山水令人印象深刻,而园中的汉语匾额和屏风上时不时出现的诸如“尧舜禅让”“竹林七贤”之类的汉文化典故又让人感到分外亲切。如果童寯有机会和村松梢风一同逛园子,他应该会非常赞同对方的观点——虽然是两个一衣带水、在文化上有诸多关联的国度,日本园林亦在吸收中国造园艺术的基础之上,发展出了一种独树一帜的审美意趣。 中国园林的开端始于公元前1800年夏桀建“玉台”。700多年后,周代开国君主文王建“灵台”“灵沼”“灵囿”,均在《诗经》中有所记载。秦始皇的“上林”集合台、池、林、囿,是一座规模宏大的皇家猎苑。汉武帝继承了这一遗产,以此为基础整合其他离宫别苑,装点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出于对长生不老的寄托,武帝命人在水池中堆砌出石岛比拟蓬莱仙境,这一主题之后成为中日两国造园传统中“池-岛”手法的渊源。 同样从汉代起,园林不再是帝王的专属之物,文人园开始出现。据传,董仲舒为了专心致志而免惑于园,在室内垂帘三年从未拉起。不过当时的文人园在设计上非常简单,不过是堂前种一些植物而已,远远不及现在我们看到的园林这般精致繁复。晋代开始流行私家园林,待盛唐时,园林别业遍布都城长安及其近郊,文人雅士筑园无数,其中的佼佼者当属王维的“辋川别业”,他所作的《辋川图》大大增加了这座园子的美誉。唐代的另外一位著名诗人白居易则无论身居何地,都必造园,不求精雕细琢,只取亲近自然之意。 北宋时期,洛阳私园众多,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介绍了洛阳的25座园林,其中数座始建于唐。都城开封最有名的园林当属徽的“艮岳”,然而它很快就随着金兵入侵而。随着、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南宋时期的名园多出自江南地区,这亦为其后江南园林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基础。到了明清初期,江南园林达到了顶峰,其中以南京、太仓、苏州、扬州、杭州和上海为最,并定义了如今我们所理解的中国古典园林。1634年,计成著《园冶》,造园学始成系统。 在童寯看来,中国园林可以说是三维版的中国山水画卷,“透过空间与体量,一瞥之下,全景转为一幅消除景深之平面,游者将深感惊奇,园林竟如此酷似山水画。”园林中的标志性元素——曲径、茅屋、垂柳、异石——都能在山水画中一一找到对应。因此他认为,只有文人(而非园艺学家或景观建筑师),才能筹谋出一座中国古典园林,“情趣在此如此重要,远甚技巧与方法。” 和园林相比,中国园林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虽然意图模仿自然,但全然摒弃前者的山野丛林之气,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国园林不是一个宽敞的空间,而是由廊道和高墙分隔成若干庭院,主导景观、形成观者视觉焦点的是建筑而非植物。因此,中国造园大师鲜有注重园林植物者,这不是说植物不重要,而是说花木仅起附属和辅助的作用。它们以看似自然的方式生长,增加园林的野趣和诗情画意。 对于文人来说,中国园林是在现实中再现的某种,是一个想象的微观世界,是一种模拟自然的艺术。园林入口处通常力求低调不显眼,待访客以一种轻松的进入后,用不断变化的风景带领他们获得一种“如坠梦中”的奇妙感受。然而这种感官刺激是十分委婉的——中国园林常常以高墙环绕,各院落之间如果没有建筑相隔,两侧则设廊墙,以为间隔。墙上或设门洞或设漏窗,诱使访客透过门洞或漏窗进行窥视。门洞常以满月、宝瓶或花瓣为形,漏窗则常以薄砖、瓦片砌成精美的图案。当门洞或漏窗框出庭院的些许风景时,增强了园林的空间纵深感,不断吸引访客继续探访前行,继续发现惊喜。 “中国园林并非大众游乐场所。园林令人钦佩地用纵横轴线和十字道解决的交通问题,在此全不存在。因为游人是漫步而非径穿。中国园林的长廊、狭门和曲径并非从大众出发,台阶、小桥和假山亦非为逗引儿童而设。这里不是消遣场所,而是退隐静思之地。”童寯说。从这个角度来看,苏州同里退思园的命名很好地点出了中国园林的“退隐静思”之意。清光绪年间(1885年),安徽兵备道任任兰生回归故里修建宅院,他将自己的私家园林命名为“退思园”,取《左传》中“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之寓意。 中国造园艺术很早就到了朝鲜、日本、越南,其中日本园林在吸收了中国园林艺术的精髓后,逐渐演变出了一种独树一帜的风格。推古女皇二十年(613年),苏我马子从朝鲜到中国学习造园法,在日本建成第一座庭园。该园承袭秦汉典例,在池中筑岛,效仿中土的海上神山。 日本园林自成系统,法式严谨,并随朝代演变,按地势可分为平庭、筑山庭,按手法可分、行、草三体,在历史上先后出现了一系列造园派别,如平安朝(8-12世纪)皇室贵族的离宫寝殿式神泉苑;镰仓时代(13世纪)佛教方丈庭;室町时代(14-15世纪)的禅枯山水;桃山时代(16世纪)的茶庭;江户时代(17-19世纪)因明代遗臣朱舜水渡日而兴起的文人庭。日本园林的命名、建筑物题额和配景说明皆用古典汉语,表达对中土文化的推崇之意。随着历史演变,造园艺术也从达官显贵走进寻常百姓家,即使是普通民居屋前的分寸之地,也能点缀花木,形成袖珍式“箱庭”。 室町时代的相阿弥(?-1525)和江户时代的小掘远州(1579-1647)把造园艺术精极简,赋予其更多抽象的象征性意味,可以说是已经超越了中国影响。然而中国造园艺术仍然在给日本造园家们源源不断的灵感。计成的《园冶》于崇祯七年(1634年)出版,流入日本后被称为《夺天工》,可见其在日本的评价之高。明遗臣朱舜水将江南园林的造园风格至日本,有着“江户名园”之称的东京小石川后乐园至今仍然存在圆月桥、西湖、园竹等中国风格元素。 但与中国园林一脉相承的是,日本园林同样以建筑为主,以植物为辅。“中国园林中,建筑如此赏心悦目,鲜活成趣,令人轻松愉悦,即便无有花卉树木,依然成为园林,”童寯指出,“此在日本尤切。京都龙安寺园内,完全摒绝植物,只现石、砂,以及一道夯土墙。该园借用紧接边界外之茂密树林,以资弥补,保持高雅。” 枯山水庭园被认为是日本园林的黄金时代,这也与中国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佛教于552年由中国经百济传入日本。6个多世纪后,日本又从南宋接受了禅和饮茶的风气,为后来室町时代的茶道、茶庭打下了基础。宋、明两代山水画家的作品被临摹成日本水墨画,用作造庭底稿,通过石组手法,布置成茶庭、枯山水。 “日本的庭院,在狭窄的空间内制造出有山有谷的感觉——这被称为枯山水。正中间都是白砂,用白色砂砾表现出瀑布的感觉。也就是说,日本人试图在狭窄的空间内再现大自然的本来姿态。当然,这些山石都是人类寻来特地安置在此的,却要制造出令人觉得完全就是自然形成的山山水水的效果。这,就是日本人的审美观。”日本美术史学家高阶秀尔在《日本人眼中的美》一书中这样介绍枯山水。 在童寯看来,枯山水期待观者能够发挥想象力,自行探究象征性艺术的内涵,以达到佛教所追求的悟境,这把日本园林艺术推向了顶峰。日本枯山水大师枡野俊明、七月合作社创始人康恒在接受“知中”采访时表示,枯山水是禅的表达载体,其的思想境界,与善于、深思、顿悟、、用心的日本人的习惯不谋而合: “枯山水的产生,一方面,是在萧条悲凉的背景下,的确需要创造出一种新的园林形制以静思人生、摈弃;另一方面,是透过后世无数观赏者的视野,枯山水园林的造园师设计时的内心世界;再者,也希望凡目睹这枯山水的人们,能够结合个人的人生经验,融于庭院意境中,人生。枯山水,向来无色无花,但置身其中的人,往往能够形势,将其作为一种场所或者仪式,找到价值的内涵。” 村松梢风以作家特有的敏锐观察力,一眼发现了中国园林宜于从外面观看,日本园林宜从屋内向外观看的区别。他指出,只有将所有的景物从某一特定的视角统一去观赏,才能了解日本庭园的旨趣,这是因为日本园林本身就是以观赏庭园本身作为造园目的的。然而这样做的代价就是,日本园林在建筑物与庭园之间的和谐、树木的阴影等方面落于下风,建筑物仿佛都“地呈露在空间中”。 与之相对的是,中国园林是用庭园去衬托建筑物的价值的。“林木掩映着楼阁,泉水倒映着堂榭,它力求做到从外部眺望时能如一幅画一般和谐隽秀,并且从屋内望出去也绝不会失去雅趣。正因为它不像日本庭园那样去比附模拟宏大的形象,所以反而可以充分体味闲寂清雅之趣。”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村松梢风进而发现,西湖——可以说是一个放大版的园林——的湖光山色亦不过是使所有的建筑显得更美的背景而已,“游了西湖之后我才真正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建筑之国”。 有趣的是,在很长的时间里,日本园林甚至是不能行走的——镰仓时代以前,日本园林的园景只有一面,仅供自茶席观看,是不可登临的“眺望园”。之后才出现“回游式”庭园,铺设径道,供访客行到园中观赏景色。童寯指出,“16世纪以前,日本园林全无可供步行之径,令人惊奇,难为现代心理所解。自曲廊之某一固定视点,观赏如画之景色,已令游者心满意足。”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可能是无解的。毕竟中国园林绝对不可能在一个固定地点看到全景。眼中所见,仅为整体中的一个局部,每往前走一步,景色次第展开,引人入胜。因此“移步换景”才是中国园林的正确打开方式,正如童寯所说:“中国园林空间处理,皆将观者视域局限于仅为单一画面之庭院中,旨在充分体现隐匿与探索之主题。游者于中,将始终乐此不疲。迭生,迷津不断,所穷无尽。”在他看来,和中国园林的变化多端相比,日本园林成规更多、变化更少,反而有种“森林般的质朴”。 而当你游览一座日本园林的时候,你常常会发现游客们会坐在游廊上,面对着一隅枯山水沉思良久。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副教授董豫赣在12月8日于苏州慢书房举办的《东南园墅》新书发布会上就指出,与日本园林不同,中国园林缺乏那种“性的东西”,甚至不适合用“景点”去描述其中的景致。游览中国园林,无需线,也无需长时间停留在某地,你需要做的,是随心而动,自己去发现风景。 除了观看方式这一决定性差异之外,中日园林还在细节中体现出不同。高阶秀尔指出,中国的建筑有一些屋檐极其长,反翘弧度极大,极端卷曲,但日本的反翘弧度只有极微小的一丝。对于日本建筑而言,屋顶是关键性组成元素,通常宽大而房檐深邃,屋檐的直线向两边水平延伸,左右端微微上翘。他认为,这种微妙的弧度深刻地存在于日本人的审美意识中,例如日本刀自平安时代起出现弧度,由汉字演变出来的平假名也有着类似的曲线。 童寯发现,虽然中日造园艺术中都重视对石头的运用,但中国造园家喜欢用经水力冲蚀而成的“湖石”,讲究石头的“漏、透、瘦、皱”。而日本园林中的石山或散石皆没有水力的痕迹,看上去与野外的天然石无异。不过,他也发现了广泛引用于日本园林、却在中国园林中难觅踪迹的东西——石灯笼。“值得存疑之处在于,中国园林从未考虑夜间地面之照明。日本石灯,原为中国之附物,却于中国庭园中未获采用,实为意外。” 所以中日两国的园林有什么不一样?童寯对此的回答是,虽然日本园林源于中国,但它追求内向景观,整体依然开阔宽敞;而中国园林的格局则基本上是一座由院廊环绕的迷宫。“事实上,日本园林具有与相似的‘原始森林’气氛,但它赋予‘原始森林’以神秘含义并成功地构成一个缩微的世界。” 《日本人眼中的美》,【日】高阶秀尔 著,杨玲 译,浦睿文化/湖南美术出版社,2018年10月
|